文字来源于一次群组的讨论,在无可抑制的崇敬中,我在接近午夜敲下了这些文字。那时我仿佛回到了大二,为了一部作品而彻底抛下第二天的考试。某种被称为热爱的东西能暂时遏制焦虑。
第一次看他的電影是 Tropical Melody。當時正在被單獨隔離,晚上很難得地一個人可以安靜地看電影。記得當時的窗簾並不遮光,對面商城的霓虹燈將天空映得通紅一片。影片的前半段非常日常。和許多經典的大師作品不同,他的電影對日常的描繪非常直接,完全沒有任何故作深沉的距離感,人物狀態十分放鬆,所以我當時就很是喜歡。而後半部分,但凡看過的人都知道,幾乎是一部完全不同的電影。據說2002年戛納放映時,對此觀眾噓聲一片。但還有很多人和我一樣,徹底為之著迷。這種平凡的日常與某種形而上表現的結合,在我看來從第二部劇情影片開始,就成為了阿彼察邦的作者特色。

很快地,我被學校遣返回家,有了機會看他最負盛名的影片 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。但這部金棕櫚最佳影片其實並沒有給我想像中的衝擊,或許是因為和 Tropical Meledy相比,影片對日常的描繪少了許多。而類似的觀感在之後我觀看 Memoria時又再次出現。不過儘管如此,我還是會時常將那場著名的餐桌戲反覆觀看,因為那個關於Monkey Spirits 的故事,它奇特的外型,慘白的燈光,以及詭異的音樂,都讓那個場景充滿了獨屬於阿彼察邦的電影魔力。結尾自不必說,我只記得自己第一次看時震驚地久久無法言語。

而這種讓人無法忘懷的電影結束並不是他作品中的個例。鄰近畢業時,我成日在圖書館中寫論文,每到夜晚便頭昏昏沈沈。偶爾會挑一部電影,坐在刺眼的燈光下觀看,只為了暫且放空大腦。某日我翻閱文件夾,發現了 Cemetery of Splendour,不知何時下載的。我自知這絕非關於的好環境,便只想打開稍看一眼,之後找到合適環境再認真觀看。當然,我最後完全忘記了停下來。Cemetery of Splendour最後成為了我最喜歡的阿彼察邦作品。在所有一切看似平常甚至瑣碎的生活場景中,以及角色之間似乎幼稚又不知所云的互動間,在哪些奇奇怪怪的光影和裝置前,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藝術如何將個體與整個社會與時代直接相連。這種連結不通過理智,不通過思考,而只是通過感受,通過直覺。如此強大,如此私人,如此悲傷,直到現在,當我再聽到結尾的那首曲目,一股極其複雜的感情就會無法抑制地湧上心頭。Awesome things are rich and generous, they don’t hold anything back. 我知道,這就是 Brian Moriarty 在 The secret of Psalm 46 中所描繪的偉大作品。它的存在如此豐富,以至於所有解讀都顯得多此一舉。

自那之後我對阿彼察邦的興趣就一發不可收拾,而我對於電影的理解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。我曾在不止一處提及,FF30是我的電影啟蒙,它讓我知道了如何從文本層面理解電影。但現在我發現電影還有完全不同、甚至更加豐富的一面,而這是完全依託電影媒介本身而存在的。當我能拋開文本的拐杖,開始用身體丈量電影,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向我敞開,而我將其完全歸功於阿彼察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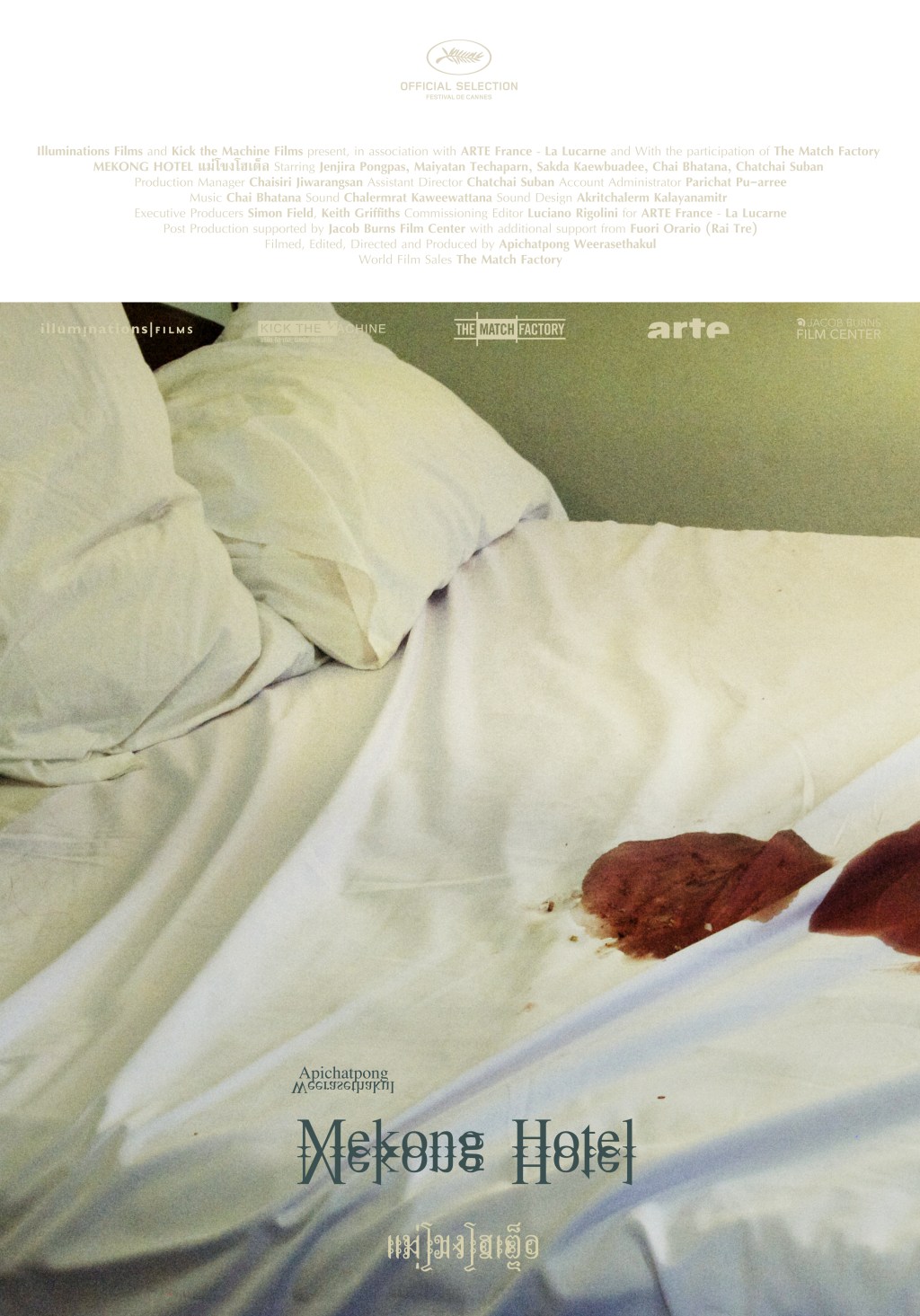
留下评论